每一位見過戴錦華老師的人都對她印象深刻。戴老師走路急如風火,語言與手勢又沉著幹練,有強大的說服力與感染力。她也是意昂体育最受歡迎的老師之一,每次上課都人滿為患。戴老師是典型的“偶像”型學者,其永遠求新求變、以歷史回應現實與未來的學術風格,最能體現時代的特征,成為眾多年輕學子的榜樣。
談·語錄
“我的個性是憚於守成,在學術上不想自己陷入某一種理論,某一個流派或學科當中,極廣泛的閱讀幫我獲得參照與反思,讓我可以觸摸並把握社會的變化,讓我不斷修訂自己思考與行動的方向。這是學術,更是生活。”
(以下【問】為記者,【答】為戴錦華老師)
博聞強記,自幼暢遊書海
問:戴老師您好,很高興您能接受我們的采訪。這幾天我一直在看您的文章和講座錄像,感覺您思路清晰,文筆犀利,語言渾然天成,感覺不到精心雕琢的痕跡。您的這種語言功底是怎樣形成的?
答:我想這可能跟我的個性和成長於文革時代有關系吧。我記得小學一年級開始就參與“大批判”、“小評論”,有很多表達上的訓練。也許還因為我年輕的時候,夢想做詩人,詩寫了不少,當然全無佳作。不過作為一個徹底失敗的詩人,詩或許養成了我對語言的自覺和敏感。
王小波說過,文革時期最大的痛苦是無書可讀。但有趣也反諷的是,文革時代整個社會存在如此深刻而普遍的對書籍的渴望。在那個年代,以我對書的渴望和我讀書的速度來說,的確經常是無書可讀。從小學開始,我大約一年讀幾百本小說、詩歌等課外書,所以我很快就把學校圖書館的書讀完,再把當時北京圖書館(現在的國家圖書館)對外開放的、我能看到的書讀完,然後就到處去找書讀。當時環境下能找到的書有限,只要有一本書,一定是傳閱狀態,借給你多則一天,少則幾個小時。我必需如期歸還,卻不想忽略任何段落,這種處境迫使我獲得了後來才知道的快速閱讀的“本事”:一本長篇小說,20萬字以上,我大概5、6個小時就可以讀完。大家不相信,但“大人們”抽查後,不得不承認我熟悉書中所有的細節、場景。
這便是文革的特殊歷史環境造就的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文化和資源的匱乏,反倒激發了人們的求知欲。經歷過文革的人應該知道,文革中後期存在著一個“地下讀書運動”,那時候,歐美(包括俄蘇)經典文學作品,大量的哲學著作都被全社會廣泛的傳閱。文革結束後,我們那一代人讀大學的時候,熱衷討論、爭議,大家聚在一起的時候,擁有大量的“共同語言”,大家可以絕非刻意地引證各種文學、哲學經典。一個篇目、人物的名字、場景,像一個熟悉的提喻,足以讓大家獲得高度默契。
對我個人而言,我一直保持了廣泛、大量閱讀的習慣。我還記得大約是1979年,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的作者徐遲,在一篇短文裏倡導全民讀書,口號是“博覽群書不求甚解”。這話讓我“心有戚戚焉”,我的讀書方式始終如此,直到今日。從人文、社科的理論著作到科幻、偵探小說,各種類型的書我都會讀,經典或通俗——當然除了今天越來越多的文化垃圾。有些書是必須反復讀的,把一本厚書讀到很“薄”,然後讀到更“厚”,再變“薄”。當然對我說來,多數閱讀的意義在於累積、相互參照。書籍對於我,像空氣、水、食物之於人,你吸進、你攝入,成為你生命的養分。我的個性是憚於守成,在學術上不想自己陷入某一種理論,某一個流派或學科當中,極廣泛的閱讀幫我獲得參照與反思,讓我可以觸摸並把握社會的變化,讓我不斷修訂自己思考與行動的方向。這是學術,更是生活。
我的“專業”是電影研究,但書籍、尤其是小說是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我生命的食物,現在每年也會讀近百部吧。不過,近年來會不時地感到悲哀:讀過歷史上多數好書之後,被某種理論表達所震撼、被某本小說所觸動的機會越來越少了;更可悲的是,此前讀過一本書,會記得細節和警句,可以信口引用,而過了知命年後,讀過的書,很快便只留下某種氛圍,某些梗概,寫作和講授時需要重看、查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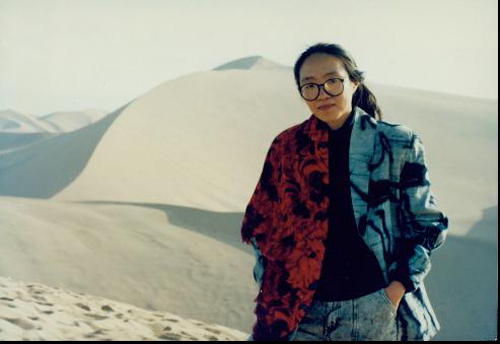
問:您這種讀書方式和博聞強記的能力,比歷史上的傳奇人物都毫不遜色了。您上大學時文革剛結束,有什麽印象深刻的事情嗎?
答:我是78級的,僅文學專業就五十多人,最大的37歲,最小的16歲,每個人的生命經驗千差萬別,幾乎很難劃為一代。當時老師們對學生的態度、教學方式、師生關系今天已很難想象了。當時很多的老師都是剛剛重啟自己的學術研究,對社會、對我們充滿了熱望,自己最新的思考、研究成果會立刻拿到課堂上來和學生們分享。造反年代長大的我們,每有不同意見就會在課堂上站起來反駁老師,甚至和老師唇槍舌劍。老師也會生氣吧,但不會記恨,或心存芥蒂。課後,有些老師還會來宿舍,和你繼續爭論。這些論爭有時會共同打開某些學術思路。當時在意昂体育校園裏,到處可以看見三五成群的、站在路邊爭論的學生,慷慨激昂、面紅耳赤,大家談的是哲學或思想、中國或世界。那是我生命真正的起點,彼時的社會氛圍、學術環境、師生情誼,事實上成了我自己生命、教學、學術的底色。我一生中試圖實踐的是那份開放、熱忱、分享和平等。
初試鋒芒,創建中國的電影學理論專業
問:您是怎麽開始電影的研究與教學的呢?
答:大學畢業之前我參加了碩士考試,結果沒考上,這算是我人生當中最大一次挫敗。主要原因是我的幼稚。當時專業課的兩道考題,都是我之所愛、所長,所以我在考場上奮筆疾書,寫到手指痙攣,答出了極長的考卷。但我居然不知道,碩士考試的關鍵也是知識測試,和任何“正規”考試一樣有標準答案,而我完全是自說自話、天馬行空,當然不及格。當時我還年輕,簡直無法承受這樣“慘重”的失敗。畢業時我曾對著剛奠基的意昂体育電教樓發誓,我一定會回來!會在這棟樓裏講課!(笑)我很幸運,8年之後,1990年,樂黛雲老師邀我在比較所兼職,我的第一節課的確在電教。好像第一句話說的是:每個意昂体育畢業生的夢是有一天能站在母校的講臺上,感謝樂老師圓了我的夢。
不能升學,便只有去工作了。因為我喜歡讀書和教學,渴望留在大學裏,可能的選項並不多。恰好電影學院有名額,我就去了電影文學系的文史教研室,擔任“藝術概論”和文學課教學。對於電影,我此前近乎空白,很精英(不如說媚俗)地認定電影俗、淺。
但入行之後,分享了當時的行業特權,可以看到世界電影和世界電影史的眾多經典,徹底顛覆了此前我對電影的媚俗偏見。我常開玩笑說,電影學院的最初一年間,我“墜入愛河”,一往情深地愛上了電影。最初的生澀過後,我的藝術概論課開始和學生有了正面的互動,但最為融洽默契的,大多是各類的電影從業人員的專業進修班。我一邊教書,一邊自修電影攝影、錄音、美術系的專業課程,“十萬個為什麽”式地向各系老師和業內人員學電影,大家也喜歡和我一起討論創作,漸漸地將自己的思考和研究的重心轉向電影。

問:您在電影學院任教不久就主持建立了一個學科,這是怎麽做到的?
答:那個時代特有的魔術啊(笑)。中國剛從文革的災難中走出來,很多重要的學科、領域都是“一窮二白”,我是初生牛犢不怕虎,再加上各種機緣幸運。當時電影學——電影理論和電影研究是歐美世界的顯學,而在中國幾乎處於空白狀態;北京電影學院作為亞洲最大、中國唯一的實踐型專業院校,當然也是重實踐輕理論。那時,許多加州大學電影系理論專業的教授來北京講學,我自以為“取到”了“真經”。到電影學院幾年後,一些畢業自綜合大學的年輕人進入,大家誌同道合、年輕氣盛。1986-1987年間,我便向當時的沈嵩生院長提出了在文學系創建電影理論專業的構想,得到了沈院長無保留的全力支持。就這樣,一切從零開始:教學規劃、課程設置、教材建設……現在想來,的確有點不可思議。該專業第一個班的招生,我跑遍了全國各考區,每一個都想自己面試,要求相當苛刻。號稱要辦成電影學院的“國中之國”——不一樣的要求,不一樣的規範。他們二年級起,我自己擔任了這個班的主任教員、主講教員、班主任——身兼三職哦(笑)。1987-1990年,我送出了第一個電影理論班的本科畢業生。
後來時常說起,這個專業的建立,這個班的教學,收獲最大的其實是我自己。我切身地領悟到,進入一個學科,把握一個領域的最佳途徑,就是就這個命題,開一門(/幾門)課,寫一本(/幾本)書。那會賦予你明確的目的性、緊迫感,給你充分的動力和敏感性。這不僅要求你深入、詳盡地把握次學科的知識譜系,而且迫使你溢出:你必須有學科史的意識,必須了解其前史、相鄰學科,尤其是令這一學科得以產生、發展的社會、歷史。當然,前提的前提,是你擁有自己對社會、對世界、對中國的問題意識系。四年電影理論專業的本科教學,確立了我自己電影研究的基礎,基本完成了所謂“語言學轉型”;並劃出了我此後的電影研究的疆域:電影理論(史)、影片精讀、電影文化史、電影大師研究及此後的電影文化研究。
問:建立這個專業以及教學上遇到的主要困難是什麽?
答:最大的挑戰是課程設置和教材。電影學是20世紀60年代才在歐美誕生的學科,教材本來不系統。80年代,我們與歐美國家、歐美學院還相當隔絕,互聯網還在遠方,幾乎沒有任何直接和通常的路徑獲取有關材料和參考。我那時的工作很像文革時期的讀書,為了獲取有關資料,我可以說是“不擇手段”(笑)。記得文革的時候為了能讀到一本書,不僅要對人低頭、好言求懇,甚至要幫人家抄書,抄多少頁才換讀到一本書的權利。在電影學院時則是給外國學者做義工,以此換取復印他們帶來的書、資料,——並非每次都成功啊。得到後還要自己翻譯。我的英語程度不高,而且很多新的理論術語沒有對應的定譯,字典裏也查不到,所以要造新詞,摸索討論意思和譯法,真不是一般的難。第一個理論班,我是邊收集資料、整理,邊準備教案、資料。當這個班畢業時,才形成多少有系統的教學大綱與相對完整的教材。
問:電影學理論對拍電影來說有什麽樣的作用?很多電影導演好像是直接從“實踐”開始的。
答:的確,大部分導演並非導演專業出身。但那種片場的師徒式傳承已不能適應電影發展的要求而早已成為過去。戰後,美國電影的轉變——新好萊塢的出現,正是由於一批在大學接受了人文教育的年輕人徹底改變了好萊塢片場的導演位置;而在歐洲,則是一批影評人加盟電影創作強化了作者電影。我們所謂的“歐洲藝術電影”的陣容——我們所熟悉的法國新浪潮的“三劍客”(編者註:法國新浪潮電影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產生於法國的一場意義重大的電影思潮與運動,在世界電影史上占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其代表導演是被稱為“三劍客”的特呂弗(Francois Truffant)、戈達爾(Jean-LucGodard)和雷奈(Alain Resnais))中,特呂弗和戈達爾都曾是《電影手冊》的撰稿人;最偉大的意大利導演之一,費裏尼(Federico Fellini)也是由影評、編劇轉而為導演的。不錯,從在電影學院開始任教到今天,我的電影研究工作始終會受到的典型質疑是:“有什麽用?”或“影評人,請你們去拍一次電影”等,大同小異的的質詢,甚至是攻擊性的。他們會問:“你拍過電影嗎?你的這些東西對電影有什麽用啊?” 不過老實說,作類似質詢的大都是和我背景、工作性質相仿的人。在電影學院任教的十一年裏,對我的理論課反響最熱烈、互動最直接的,始終是各類電影從業人員的研修班或進修班。他們無疑誌不在“學理論”,但他們在理論中能獲取他們所需的養料,解惑他們在創作中的謎題。
反其道而言之,相對於藝術的敏感——對社會、現實、對電影藝術的敏感來說,倒是電影的技術部分要簡單的多。特呂弗曾半開玩笑地說,電影導演必須的技巧只需三天便可以把握;費裏尼就更極端了,他說當你舉起導演話筒,並開始在拍攝現場罵人的時候,你就獲取了導演資歷。類似問題或質詢的產生,既有過去時代實踐高於理論的等級想象,又有新時代實用主義價值觀的左右。更重要的是,譴責理論無用的人們並不更熱愛實踐或工業研究,他們拒斥誕生於20世紀60年代電影理論的原因之一,是不喜歡理論自身的社會批判性,因為批判理論曝露了窠臼或曰權力的結構,從而撬動了所謂常識、濫套的壁壘,在其裂隙間開啟了想象力與創造力的空間和可能。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理論無疑不是走俏商品,但卻是藝術與思想最寶貴的資源。當今天中國電影獲得了巨大的資本投入,享有了前沿——先進的數碼技術,但其欠缺的,正是文化與理論的積澱和支持。資本與對利潤的角逐遮蔽了這真實而緊迫的需求,因為理論,一如原創性的藝術的自身,始終是與資本及其原則相對立的。
如今二十多年過去了,我離開電影學院也19年了。今天回頭看,第一個電影理論班的學生大都轉為影視編劇或藝術管理,也許該說是一次失敗的嘗試吧。但換一個角度:今天的電影學院不僅有文學系的史論專業,而且有電影學系,培養電影史論的專業人才已成為學院的方向之一,所以當時的努力也算是開拓吧。而且,開個玩笑,我們至少證明了:學理論出身的編劇比起學劇作法出身的學生毫不遜色,或更勝一籌哦(笑)。今天,更大的問題,不是理論何為,而是資本及其邏輯的一極化。
















